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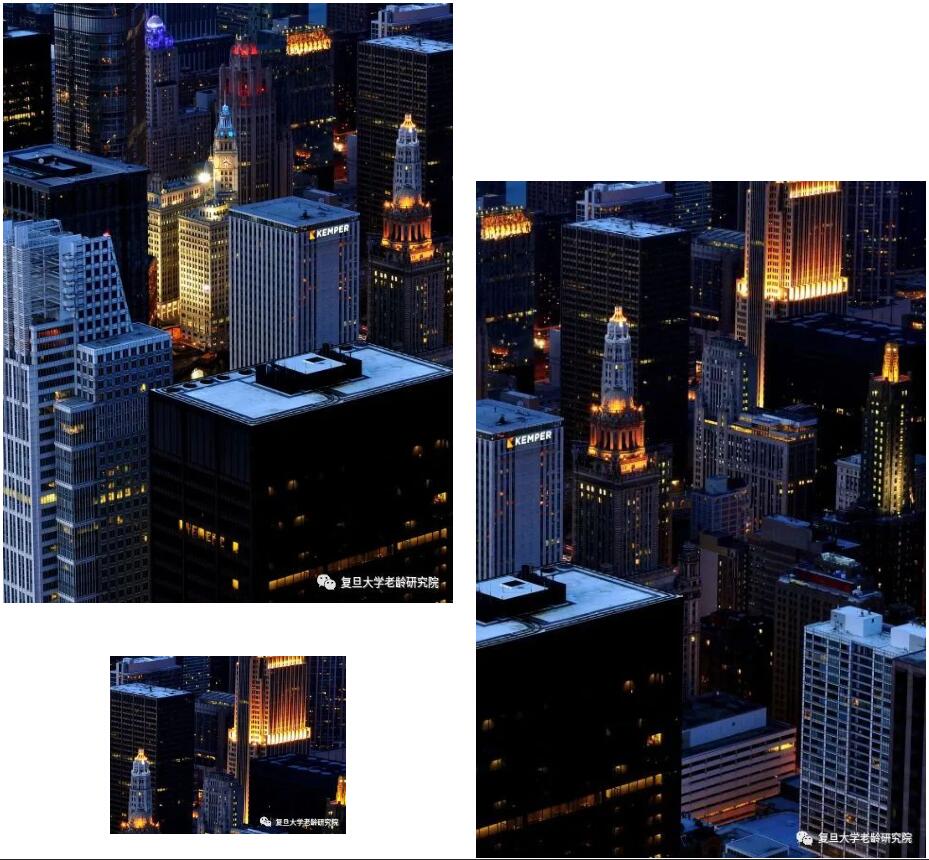
19世纪末以来,人类寿命大幅延展而生育水平显著降低,两者叠加使全球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这一人口态势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概无例外,区别只在呈现之早晚与进程之缓急。2015年,全球尚有115个国家和地区未进入老龄化阶段,但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将骤降为33个。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后,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升至13.3%和8.9%;到2020年“七普”时,分别达到18.7%和13.5%,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超过2.64亿 。不仅如此,老年人口的增长率明显快于总人口的增长率,而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长率又明显快于一般老年人口。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分别接近5亿和超过1亿。作为人口再生产模型转换的必然结果,人口老龄化将长期持续且不可逆转,尤其以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为代表的“长寿型老龄化”(也称“顶部老龄化”),正逐渐取代以生育率走低为标志的“少子型老龄化”(也称“底部老龄化”)成为老龄化发展的主导动因。个体的长寿化与人口的老龄化,在当代社会正趋于常态化,甚至可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之一。
老龄化治理认知不断深化
基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寿命延展和老龄化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概念框架,即“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幸福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过程”。随着研究实践不断发展,其内涵与外延亦不断变化,老年人不仅要健康活着,还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到家庭和社会活动中以充分展现价值。WHO由此在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即“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联合国将其推广为全球行动框架并不断发展之。“积极老龄化”无疑是以“健康老龄化”为基础,发展出“健康—保障—参与”三支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老龄化治理的认知深化。有效的“参与”必以“健康”和“保障”为基础,而同时“参与”的成果则又以更好的“健康”和“保障”为诉求。这一方面使“积极老龄化”不再局限于老年人群体而成为一个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议题;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积极老龄化”亦不仅重视“老有所养”或“老有所依”,更强调“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不难看出,“健康老龄化”侧重成长的延续性,强调晚年的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强调参与,它使老龄化应对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这些目标显然无法通过仅仅关注老年人的社会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全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最具共识的老龄社会治理框架。正是在此基础上,WHO进一步整合提出了“老年友好世界”(Age-Friendly World)的概念。其实,更准确的应译为“全龄友好世界”,现译法内涵以“老年友好”为基础和核心。在研究实践中,则更多被称为“老年友好型社会”或者“全龄友好型社会”(Age-Friendly Society),即一个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积极参与并被尊重的社会;一个让老年人更容易与对他们重要的人保持联系的社会;尽可能地帮助老年人保持健康活力,并为那些需要照护和帮助的老年人提供适当支持的社会。中国政府较早即对“老年友好型社会”或“全龄友好型社会”做出了反应和本地化解读,甚至“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共建共治共享”等宏观治理理念亦涵盖其逻辑内涵。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新的基本国情,其治理重要性不断升级: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特别提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和发展需求,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和主题之一。
形成中国老年社会治理特色
从本质上讲,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个体的各项能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没有哪个年龄阶段群体的各项能力都高或都低,也没有哪项能力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上升或一直下降。个体的老化更是一种逐步的、因人而异的过程,老年个体之间、老年群体之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有着显著的异质性。今天的老年人口主体与过去的老年人口主体已经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的特征,而这种差异因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人群的加入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只有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龄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老年人”与“被供养者”画上等号,人们自立自强的意识就可能增强、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可能减少、平均健康水平就可能提高,社会运行的成本才可能降低,从而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不仅如此,迈入老年也不必然意味着衰退与病痛,老年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不断扩充的、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而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发挥。当然必须指出,并非所有老年人都适合推迟退休,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途径也不仅仅包括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业是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而且还应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将老年人可以灵活就业的工作、某些无报酬的志愿劳动乃至部分家庭劳动也纳入“就业”的范畴。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仅是消费者,而且同样是生产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老龄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之一,正是将这些角色统筹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在强调人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潜能和参与发展的同时,也要使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尤其对老年人而言,尽管其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其政策价值仍有待挖掘,以有效控制社会成本。2010 年,我国60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的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年,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2.53年,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人口寿命提高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成本及压力,即“胜利的成本”(Cost of Success)乃至“胜利的失败”(Failure of Success),而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尚未对我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提升这一现实进行有效挖掘,对其可能带来的压力也未及时反应。这尤其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和老年科技发展的滞后性,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长寿风险”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伴随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进程,对其有效把控并合理应对极具挑战。
历史已反复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如果我们以一种创新而开放的框架来看待人类寿命延展和人口老龄化的治理议题,那么其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而是让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社会从观念上重新进行认识,并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联合国曾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这倡导了社会的包容与平等,是所有人给所有人以机会。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则正在此基础上升格强调“不分年龄人人共建共治共享”。这不仅蕴含中国老龄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与框架,更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生动注解和创新案例。